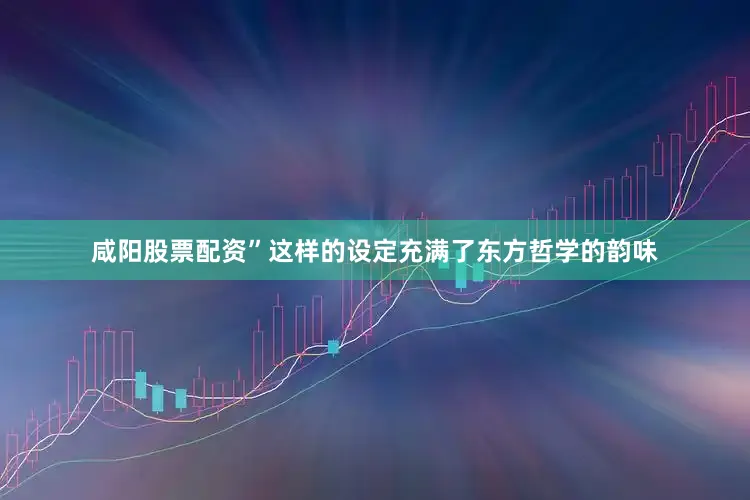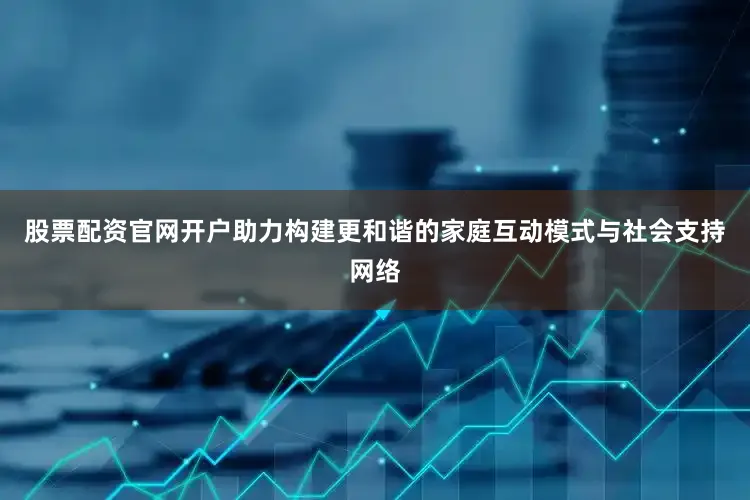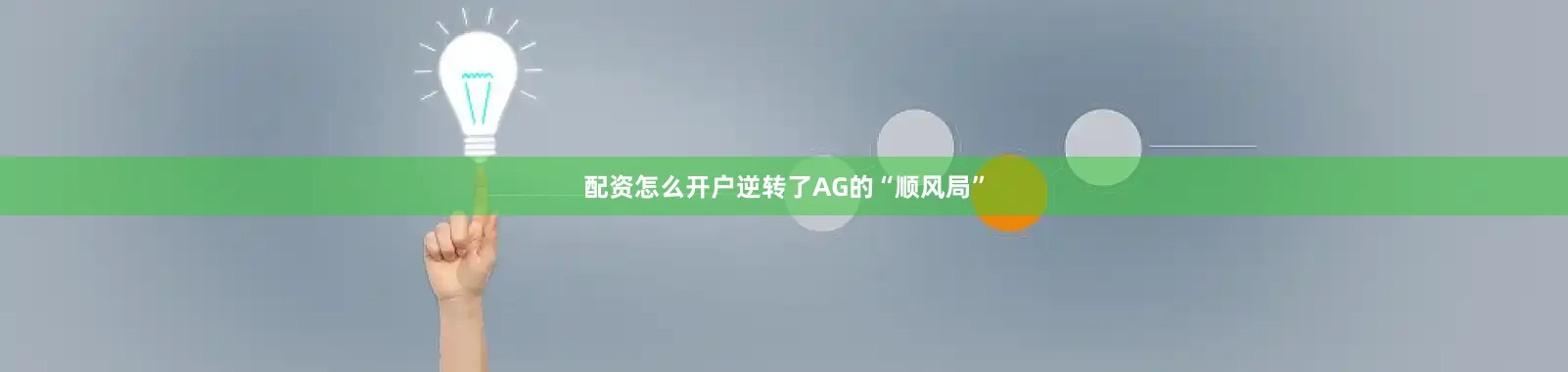一
北宋徽宗崇宁年间(1102-1106),文人雅玩之风达到顶峰,赏石、品茗、挂画成为士大夫的日常标配。
时任无为军(今安徽无为)知州的米芾,不仅是与苏轼、黄庭坚齐名的 "宋四家" 书法家,更是以 "癫狂" 著称的奇石痴人。
在这个理学兴盛却个性张扬的时代,他对一块奇石的顶礼膜拜,意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 "物我合一" 的经典注脚。
二
据宋代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卷十记载,米芾赴无为军任职时,听说州府衙署内有一块奇石 "状类岱岳",当即更衣换鞋,对着石头下拜,口中尊称 "石丈"。
下属见状偷笑,米芾却正色道:"此石足能傲立千古,吾当以师礼待之。"
更富戏剧性的是,米芾任内曾见另一块奇石 "窍穴天然,峰棱如削",竟不顾官体,双手捧石入怀,大呼 "吾欲见石兄二十年矣!"
此事经《铁围山丛谈》传播后,"米颠拜石" 的典故不胫而走,成为文人狂放不羁的象征。
展开剩余78%甚至有野史记载,米芾因痴迷奇石荒废政务,被弹劾后反而自嘲:"石兄伴我,胜却人间万户侯。"
三
《石林燕语》原文
"米芾守无为军,初入州廨,见立石颇奇,喜曰:' 此足以当吾拜。' 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,每呼曰 ' 石丈 '。言事者闻而论之,朝廷亦传以为笑。"
《宋史・米芾传》补充
"芾性好奇石,至州廨,见奇石,即罗拜其下,曰 ' 吾欲见石兄久矣 '。又不能与世俯仰,故从仕数困。"
两段记载相互印证,既展现了米芾对奇石的痴狂,也暗示了他因个性张扬而仕途坎坷的现实。
宋代文人笔记中类似记载多达十余处,足见 "米颠拜石" 并非孤例,而是宋代奇石文化的集中爆发。
四
米芾拜石,本质是道家 "物我两忘" 思想的行为艺术。
奇石的天然形态,暗合道家 "道法自然" 的哲学,而对石头行跪拜礼,正是文人试图打破 "人为贵、物为贱" 的世俗观念,追求人与物的平等对话。
如苏轼在《怪石供》中所言:"天地之间,物各有主,苟非吾之所有,虽一毫而莫取",但米芾却以 "占有式膜拜" 重构了人与物的关系。
宋代文人将赏石提升到 "瘦、透、漏、皱" 的审美体系,奇石成为身份与品位的象征。
米芾撰写的《石谱》,更是中国第一部赏石专著,提出 "石尤近于禅" 的理念。
他的拜石行为,既是对自身艺术品位的极致宣示,也暗合了徽宗朝 "花石纲" 盛行的社会背景 —— 当皇帝都在全国搜罗奇石,文人的 "石癖" 便从个性张扬升华为时代风尚。
米芾虽为进士出身,却因 "不能与世俯仰" 而辗转地方官,拜石行为可视为对官场规则的隐性反抗。
就像陶渊明 "不为五斗米折腰",米芾选择向石头折腰,实则是将奇石作为精神避难所,在 "礼" 与 "狂" 的冲突中,构建属于文人的精神乌托邦。
五
元代画家倪瓒作《米芾拜石图》,着重刻画米芾免冠跣足、对石长揖的场景,强化其 "越名任心" 的形象;
明代吴伟《米颠拜石图》以泼墨技法表现奇石的嶙峋与米芾的癫狂,成为文人画中 "怪诞美学" 的代表作。
这些画作让 "米颠" 形象深入人心,甚至影响了清代 "扬州八怪" 的创作风格。
《红楼梦》第二回,贾雨村论及 "米颠拜石",将其归为 "情痴情种" 一类,暗示贾宝玉 "爱石成痴" 的性格渊源;
清代李渔《闲情偶寄》专门设立 "山石部",开篇即引米芾故事,强调 "石虽不能言,许我为三友" 的赏石哲学。
安徽无为至今保留 "米公祠",内有 "拜石庭",置放仿宋代奇石,供游客体验 "米颠拜石" 的场景;
北京颐和园的 "青芝岫"、苏州留园的 "冠云峰",虽非米芾旧物,却延续了宋代以来的赏石传统,成为中国园林文化的核心元素。
六
米芾的故事是一场精彩的 "个性突围"。
在理学强调 "存天理灭人欲" 的时代,他用拜石行为宣告了个体情感的至高无上。
他的书法打破唐楷的严谨,他的拜石打破世俗的规则,最终成就了不可复制的个人 IP。
发布于:广东省晟红网-每日配资网站-杭州配资-配资门户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